上海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17年)
上海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17年) (2018年5月24日) 案例一: 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因群众举报,2016年8月17日,被告金山环保局执法人员前往原告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晶山公司)进行检查,并由金山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对该公司厂界臭气和废气排放口进行气体采样。同月26日,金山环境监测站出具了《监测报告》,报告显示,依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臭气浓度厂界标准值二级为20,经对鑫晶山公司厂界四个监测点位各采集三次样品进行检测,3#监测点位臭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25。2016年9月5日,金山环保局于当日进行立案。经调查,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向鑫晶山公司进行了送达。应鑫晶山公司要求,金山环保局于2016年11月23日组织了听证。2016年12月2日,金山环保局作出第202016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3#监测点臭气浓度一次性最大值为25,超出《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的排放限值20,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依据该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鑫晶山公司罚款人民币25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另查明,2015年以来,鑫晶山公司被群众投诉数十起,反映该公司排放刺激性臭气等环境问题。2015年9月18日,金山环保局曾因鑫晶山公司厂界两采样点臭气浓度最大测定值超标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裁判结果】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原告涉案行为进行处罚是否正确是本案最大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厂界恶臭来源于生产用的污泥,污泥属于一般固体废物,其涉案行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及第二款的规定,不应适用罚款数额更高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 该院认为,前者规制的是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行为,后者规制的是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前者有未采取防范措施的行为并具备一定环境污染后果即可构成,后者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必须超过排放标准或者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才可构成。本案中,被告接到群众有关原告排放臭气的投诉后进行执法检查,检查、监测对象是原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情况,《监测报告》显示臭气浓度超标,故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更为贴切和准确,且如前所述,本案并无证据可证实臭气是否来源于任何工业固体废物,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在确定罚款幅度时,亦综合考虑了原告违法行为对环境及社会的影响、违法次数、配合调查取证情况、整改情况等因素,决定罚款25万元,罚款数额亦在法定幅度内,遂判决:驳回原告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环境法律规范法律适用交叉竞合较多,环境行政处罚的行政案件如何选择适用环境法律规范是法官需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案核心法律争议在于,堆积有固体废物的企业厂界臭气浓度超出国家排放标准时,是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是适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前者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了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情况的处罚,后者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及第二款规定了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情况的处罚。 本案判决确立了最贴切法律适用原则。通过对两部法律各自条文的语义分析,结合案件情况,最终确定在厂界臭气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时应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进行处罚。同时,前述两部法律规定中的处罚幅度不同,适用处罚幅度更高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企业违法行为可起到更强威慑作用,符合环境保护利益衡平原则,对加强环保执法力度、提升环境治理效果具有典型意义。 案例二: 施某某诉上海保监局、中国保监会投诉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10年、2011年原告施某某在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购买了某保险产品,之后办理了减退保及期满结算业务。2013年原告又购买了某保险产品,该产品缴费期三年,截至2015年11月4日已经缴满。2016年11月19日,原告至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柜面办理领取了保险产品的祝福金和红利。 2017年3月16日,原告向上海保监局投诉称,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推销保险产品时存在诸多违法违规行为,要求上海保监局予以查处。被告上海保监局受理后,即要求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就原告的投诉事项作出说明,向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调阅相关保险产品的投保材料,调阅保单历次减保退保资料,调取有关原告的两份电话录音,调取保险业务员王某的劳动合同,对太平洋人寿上海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及涉案保全操作人员分别进行笔录询问,对王某进行电话询问,并向涉案保单通知寄发邮局调取了邮件寄发证明。根据调查取证情况,被告上海保监局于2017年6月7日作出投诉处理决定,对原告投诉事项分别进行了答复,认为并无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和工作人员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原告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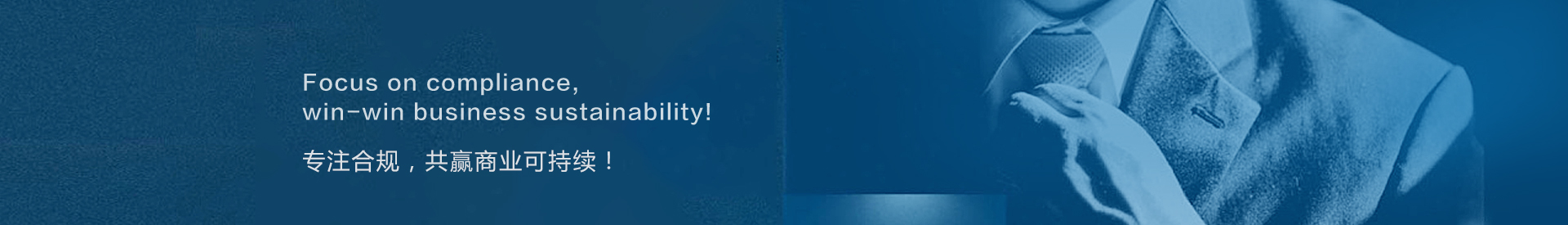
上海泽晟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绿咨力(上海)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温馨提示:合规网支持主流浏览器(IE9及以上版本),不建议使用Safari


